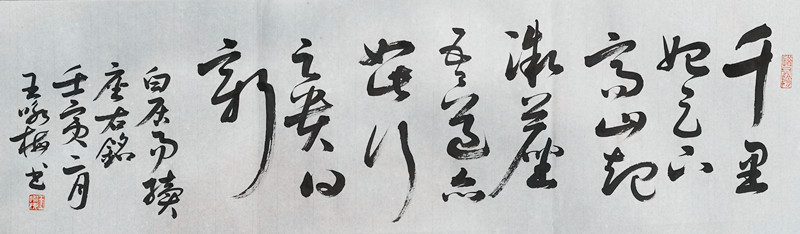
一个人的行为,绝不只是当下自由意志的产物,而是由过去、现在甚至未来意识的综合决定的。换句话说,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,如何理解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,如何看待问题,又如何处理工作与生活中的林林总总的事务,其实早已因教化与涵养的不同,在各自内心里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。
按照心理学家詹姆斯的理论,一个人的思想、行为,从根本上来说,内嵌式地存在时空含义。人的自我意识在根本上是一道“流”,而这道流的形成机制,则以自童年开始的全部经历为基质。你的每一个确定的意向,在空间上有边缘、在时间上有连续。詹姆斯将人的自我意识类比为水:“心上的确定意向,个个都是在它四周流动的水里浸渍着,濡染着。我们对于这个意象的近的远的关系,关于这意象来处的余觉,关于它的去处的初感,都与这个自由的水连带着。”后来胡塞尔将其称作“时间晕”,恰恰是这个晕圈,构成一个人处理事情的背景、材料、时机,它是潜意识与显意识的综合。
“意识”和“潜意识”都是一种主观状态。潜意识是非理性的场所,犹如一座房子的地下室,里面堆积着各种在上层建筑中所不允许存放的东西,但却在你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。意识是察觉到的经验、感情、欲望等,潜意识则是没有察觉到的经验、感情、欲望等。在生活中发生的同一件事情,但在不同的人眼里却产生不同的解读和结论,这正是因为他们受思考问题的不同机制所左右。由此观之,在事情面前,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容易怀有偏见的。这也常常导致我们在面对事情时总会犯同类型的错误。因为一个人的成长,所有经历过的事情以及周围环境、父母遗传、风俗习惯等等,皆积淀在潜意识里。越是紧急的事情,当下所作决策,因为来不及思考,就会越多地依凭潜意识构成的那个本然的自我来决策。
怎样改变自己已成型的心理机制,使其在处理事情时皆“发而皆中节”呢?
虽说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,但从根本上来说,人的行为受意识支配。而意识是由久远的经验、记忆为内核的潜意识和当下的显意识构成。其生成机制可以通过丰富当下意识和对过去的经验、记忆重新思考与认识,即“重建认知”,让自己的意识达到新的高度与层次,从而形成新的意识机制。孔子言“吾十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而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”,就是一个通过不断地“学”来改变当下的显意识;通过重建认知,就会对自己秉性之形成的基质作出反省与纠偏,从思想深处脱离原先的窠臼,形成新的意识流,从而改变潜意识的作用机制。二者结合,从而生成新的意识机制。但此事不易,需要日常生活中下足功夫。
孟子说,学问之事无他,求其放心而已。当夜幕降临,要“求其放心”,即要将放出去在事情上那昏昧的心收回来,用“理”来归顺一下,做得不好之处,找一找缘由,化解其根本处的“结”。下次再遇上同类事情,哪怕是当下即需要做决策,你所表现出的“本心”就会得到修正,犯错误或说事情处理得不恰当之程度,会逐渐得到改进,这与“格物”同理,通过闲时的“格物”功夫而达“致知”的理性高度。
孟子说人有“夜气”,即白天乱糟糟的心,到了晚上会生发、透露和聚集“夜气”,到清晨呈现为“平旦之气”。如果半夜一下子醒来,感觉到自己的本心活了,良心上感到不自在,这时的气象,便是符合“性本善”的良知气象。这便是古人修心之法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“必有事焉”,“擅养吾浩然之气”,此即《中庸》所言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。”“尊德性,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。道问学,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。”于无事处有事,思考与体悟事情之真理,达乎道之本体,遇事时即呈现“心与理一……,心包蓄不住,随事而发”,据此来处理世务,则所办之事皆可达合理合规合法合情。
我们每个人都走在修行路上,修正意识流,不断完善自己临事处置的意识形成机制,此乃不贰过之法宝也。以此与诸君共勉。